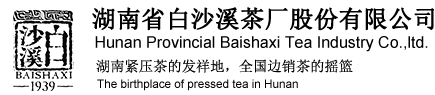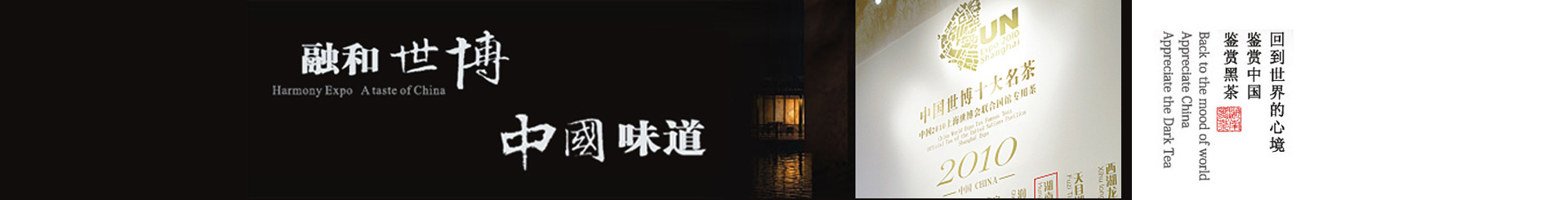27
2013/12
分享
我們奮斗在白沙溪的那些年——白沙溪老前輩走訪錄
發布時間:
2013-12-27 12:00
來源:
中華合作時報茶周刊《白沙溪》專刊 2013.12.24 B7版
那是2013年4月19日,我們遁著春天里的縷縷茶香,走進了白沙溪幾位老前輩的家,與他們聊過去白沙溪的歷史和他們所經歷的那些事,勾起了他們很多幸福而自豪的回憶,仿佛就在昨天,記憶猶新……
劉昭先:男,1924年出身,89歲,1980年退休,現住小淹白沙社區。
當我們走進老人的家,劉老的婆婆滿臉堆笑,趕緊去外面叫老倌。原來劉老正在社區門衛室與人一起打紙牌。等了一會,劉老回來了,只見老人精神爽朗,耳聰目明,看到我們格外的熱情,不用問,自已便一個勁地聊開了。
“我看到彭廠長帶領我們試制茯磚”
我是1950年進的廠,56年全部轉為正式編。我在廠里搞管理工作的時間比較長,很多過去的事我清楚。我們都知道1953年在白沙溪誕生了湖南第一塊茯磚茶,而所經歷的真實卻知之不多,通過劉老的清晰回憶,讓我們深感其中艱辛磨難,創新一個產品之不易。
老人說起1951年我看到彭廠長從仙溪押回小淹。正納悶:為什么是從仙溪押回呢?他在仙溪干啥?說著劉老聊起了彭廠長帶領白沙溪工人反復試制茯磚茶的經過。
那時彭先澤是江南、白沙溪茶廠的廠長,為試制茯磚,早在50年前就開始了,曾先后在江南、白沙溪及仙溪等地搞試驗。那年正是彭廠長從陜西涇陽請了兩個師傅仿涇陽技術,在仙溪那里租地搞茯磚茶的試制,后來還是由于氣候、溫度、濕度達不到發花要求沒有成功。因此晉陽人斷言,沒有涇陽的水,沒有涇陽的技術,沒有涇陽的氣候,你們南方根本做不出茯磚茶。白沙溪就是不信這個邪。最后我們廠派出技術骨干及壓制部主任彭南山等8個人專門到陜西涇陽,用我們自已的技術工藝邊試制邊研發。原來,陜西北方氣溫低,天氣干燥,壓制的茯磚茶只須用厚厚地棕墊上下覆蓋,達到一定的時間,便可自然干燥發花,且金花茂盛。派出人員在涇陽試制將近一年,發現并不是我們的技術工藝水質不行,其主要原因就是南北方溫濕度氣候差別所致。回來后,我們就請示中商部同意,仿茯磚發花溫濕度要求在白沙溪建烘房。把烘房建起后,1953年我們終于成功試制湖南本地生產的第一塊茯磚茶。打破了涇陽人的預言,創造了白沙溪黑茶神奇!并逐步得到普及和推廣。2008年,該項制作工藝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為了18斤茶”
黑茶是西北少數民族的生命茶,是民族團結的革命茶團結茶,中央相當重視,我們茶廠的級別也是相當高。廠里的人事安排和文件、生產計劃都是從中央下到省再到廠。52年我們的廠長是馬川,營團級南下干部(后為省茶葉公司經理,現退休)。副廠長侯斯烈過去是山西平遙的老縣長。在廠里背著東洋刀,特別威風。62年我們廠長是翟彥博,也是南下團級干部。負責我們廠保衛的是上面安排的一個警衛排,全副武裝,歪把子機槍都有好多把,機關槍好幾挺,夏天看到他們在擦拭機槍。我們的產品質量更是事關民族國家大局,加工出來的產品首先要保證少數民族人吃了滿意合格。不管出了什么問題,我們都要負責到底。
記得1960年,我在銷售科,我們調運了一批磚茶到青海,中間有個別茶出了點問題,結果是中商部從北京打電話到益陽(那時我們是一個廠),要求我們廠派人到青海處理。不久中央民族貿易局又直接打電話急催。廠里接到信的那天是1960年的12月31日,年關廠里好多事很忙,生技科派不出人,又怕這批茶的問題大,必須趕緊處理。商量把我從銷售科抽出,第二天就出發,并先從杭州調運5000擔茶后再從杭州、上海去甘肅青海。
1961年1月1日起程,往返輾轉水路、公路、鐵路,坐船、坐車、坐火車,那時國家還處在困難時期,各方面都不發達,路上半個多月趕到青海。由青海民族貿易局的人親自接待,并負責與我商量這批茶的處理方案。第二天,我們一起去看那批茶。到實地一看,只有極個別的茶出現燒心霉花。我當即答應,凡有問題的茶請你們剔出來,都由我們負責,有多少算多少。對方十分滿意。為了不影響市場供應,商定先將茶放在青海,好的先銷售,有問題的剔出來。就這樣待這批茶銷完,實際剔出來的有問題茶只有18斤。按當時價損失不足18元。但白沙溪這種以質量為重,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負責精神在少數民族人民的心目中產生了很好的印象——喝白沙溪茶放心。從此,青海人民與白沙溪結下了永遠的黑茶緣。
劉密花:女,1940年出生,現年73歲,1990年退休,現住小淹農貿市場二樓。
我家是黃谷溪的,隔茶廠只兩里來路。1951年茶廠從江南全遷到白沙溪我11歲,就跟著我娘在廠里撿茶,59年正式進廠算工齡。我雖是女同志,但我個子高力氣大,進廠就把我安排在壓制部跟男同志們一起壓茶,46歲調行政科,后到供銷科退休。
“日產10000片報喜”
那時候,我們年輕,身體好,思想單純,廠里生產、質量都抓得緊,廠長也是經常在車間轉。在壓制部,有退磚、扒茶、司稱等多道程序,各有分工。李華鴻是我們班的班長,扒茶灑面不均勻,壓出來的茶磚外觀不光滑要扣獎金,廢品超過規定比例扣獎金,退磚不快影響壓制進度挨批評。我們各組積極配合,全力以赴提高生產。那時設備還不是很好,機器是手搖式發動,一根大繩幾個人扯才發得動,有時天氣冷,蒸汽上不去,我們自已撿柴火把汽燒上去。為了加快進度,多完成任務,我們每天起碼提前10—15分鐘上班,到8點就馬上進入生產。生產中出廢品是不光彩的事,每次發現廢品趁熱打爛,用手揉勻當即加工,有時手都燙傷。因此我們生產一天只幾片廢品。記得我們文革前是日產4000片,后來逐步提高到日產5000片、7000片,8000片報喜。當時的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備戰備荒為人民”“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經常開展勞動競賽和技術比武,政治空氣特別濃厚,工作起來干勁特別大,8斤重的鉛板一次拌10片。七十年代后期的有一年的秋天,車間實行磚匣雙面鉛板,我們日產磚茶10800片,創歷史最高紀錄,車間向公司報喜,廠部敲鑼打鼓給我們送喜報,記得當時還是我念的喜報,工人們歡天喜地,生產更加熱火朝天。
楊慶生,男。1937年出身,現年76歲,現住小淹農貿大樓住屬區。
我是1961年從部隊轉業安排進白沙溪茶廠,在廠期間當過篾匠(因為我小時作過篾匠),搞過保衛、供銷、設備、生技,85年退休。
“ 由茶帶來的好處”
80年代初期,我在設備科,負責機械設備的調入,出差時我經常帶點好茶葉在身上。那年廠里派我和另外一個人去河南新鄉參加全國計劃會議,有1萬多人開會,旅館住宿都很緊張,我們湖南代表團安排在新鄉一中的大禮堂住。新鄉在河南省北部,正是隆冬12月下旬,氣溫零下30多度,南方人到北方簡直是凍得難熬。我便在外面到處走走,順便了解些情況。正巧,我走進了會議保衛傳達室。據說是北京派來的衛戌部隊,他們生起爐火室內有暖氣,我邊取暖邊拿出隨身帶的茶葉泡了杯茶,那些兵聞到茶的醇香味,直問:你咯是么子茶,這么好聞的茶香味。我隨手給了他們幾泡,戰士們一邊泡茶一邊和我聊天,茶喝得全身發熱。聊著聊著我們因茶成了熟人。快到午飯時間,他們又留我們吃中飯,那餐飯我們兩個人吃了4個大饅頭6缽白米飯。心想該走了,不曾想他們又把我們請回到傳達室,還給安排了一個大房子,升起爐火,一天一斤糧票,兩塊錢,三餐飯,我們在那住了整整七天,根本就沒有挨上凍。還搞到了600套軸承的計劃。湖南代表團的人羨慕得不得了,直說“你們白沙溪的人真的牛,我們死挨凍,你們住起暖氣房,還輕松的搞到了設備。”我在心里暗喜:其實是我帶的那包白沙溪黑茶帶來的好處。
“白沙溪改進設備歷來舍得出錢出力”
那是1967年的一件事使我印象特別深。廠里隨著邊銷茶生產量的不斷擴大,生產設備跟不上。那年我被派出沈陽錦州鍋爐廠去定制鍋爐。為了保證鍋爐質量,圍繞鍋爐鋼板我們連續跑了7個省,硬是達到標準鋼板為止。鍋爐制好后,我們在路上花了半年的時間,用6只拖輪駁船,由沈陽運長沙,再用兩只18。2噸的拖船到益陽。在益陽等了一個冬天,到春上發水,又請80、90個人背纖到桃江,船到夫溪現有人員硬是背不上,又再加40個人背纖,這樣才一個星期到白沙溪廠碼頭。當時背纖的人每人每天半斤糧食,后來請示省里加到每人每天1斤糧。這臺機器到廠前后時間一年多,花費的人力物力十多萬元。是當時鋼板厚度硬度最好最先進的鍋爐。這臺鍋爐安裝好后,生產機器發動、蒸汽蒸茶都得到了滿足,且食堂蒸飯、職工家屬生活用水都用上了熱水。生產產量質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回想起來,我們過去這些老工人為白沙溪吃了很多虧、流了好多汗,為白沙溪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不過,更感欣慰的是現在,你們在公司這班領導的帶領下,把茶廠辦得比過去更紅火,廠房建得比過去更威武,消費者對白沙溪黑茶評價這么高,每年為員工創造這么好的紅利分成,我們這些老工人感到很高興,真心希望你們把白沙溪越辦越好,越來越興旺。
上一頁
下一頁
上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