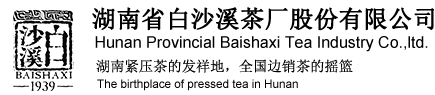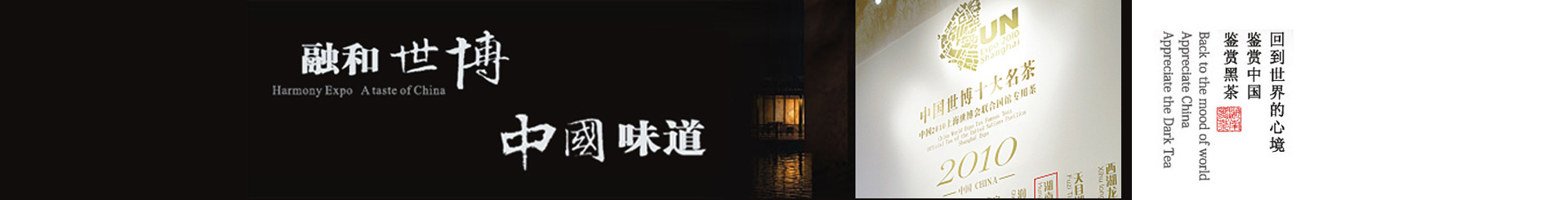01
2020/06
分享
熬茶記憶,把回憶藏在味覺里
發布時間:
2020-06-01 14:15
來源:
說到牧區最傳統的茶葉飲用方式,有很多中東部地區的漢人覺得那不高級。那是拿他們自己內心的標準在做判定,真正置身于那種惡劣環境之中,才會明白所有的傳統都是最好的安排。
早上到青海省茶葉公司旗艦店,店里的姑娘說要給我煮奶茶喝,并且強調是煮那種土土的奶茶,要煮出她記憶里的那種味道出來。
說干就干,她把泡茶臺面一收拾,架上一個簡易的灶,在下面點著一根蠟燭,用一個大號的公道杯,往里倒上開水,就放在那個小火焰上燒起來了。高原上沸點低,很快就看見玻璃公道杯里沸騰起來了。姑娘準備了姜片,用的是白沙溪天茯,熟練的將茶塞進茶包,用開水淋了一下,然后就開始放進公道杯煮起來了。
沒多時,沸騰的茶水開始散溢出煮好的姜茶味道。待茶的濃度達到她覺得合適的時候,她把事先準備好的鮮牛奶倒了進去。店里的姑娘對奶茶頗有研究,說熬奶茶并不是簡單的把奶和茶混在一起熬,奶倒進去之后,還是要注意掌握火候,將奶的營養物質發揮到最好。

她在她認為恰到好處的那個時間點上熄了火,然后奶茶就熬好了。倒在品茗玻璃杯里,濃郁的茶與奶融在了一起,佐料也發揮得恰到好處,喝起來像是一碗高湯。大口大口的喝上兩杯,渾身暖暖的,有飽腹感。
這是店里的姑娘在憑借著自己的記憶任意發揮,關于這個茶,一開口說起的就是小時候的事。熬茶是她小時候在家里大人耳濡目染之下學會的。沒有那么詳細的指南,沒有那么嚴謹的程式,沒有那么繁復的注意事項。若講茶之藝源于生活的話,今天早上她做的這一系列動作就是一個很好的茶藝作品了。我們最容易忽略的就是生活中早已習以為常的美,總覺得遠方要比腳下更美。
到青海以后,我更關注的就是寺院和牧區,這兩個地方的生活方式是變化最慢的。不過就在今天下午,我還約見了一位馬姓回族老先生。他的祖先,就是茶馬古道上的主角,往來穿梭于產銷區之間,將外面的鍋碗瓢盆和茶葉運進青海,然后再把青海的食鹽運出去。和老人聊天的時候他提到,成都鹽市街以前就活躍著很多青海鹽商。他的父親,也是一位活躍在古商道上的商人,剛解放那會兒,他才幾歲,有跟隨父親長途奔波的記憶。
他知道我喝過了塔爾寺的大鍋熬茶,也喝過了牧區藏族的熬茶,他要給我親自展示青海回族的熬茶。平日里他也常喝熬茶,他客廳茶幾上放著的電鍋就是專門用來熬茶的。他說:“我們回族熬茶,和其它又不一樣。”只見他拿起電鍋的內膽走進里屋,將熬茶用的料全部放在了鍋里。有一小塊磚茶,有生姜片、有草果之類的各種藥材,他如數家珍的給我一一介紹了他熬茶的用料,最后又著重強調了放在鍋里的大塊晶體食鹽。看上去和冰糖很像,傳統回族熬茶就需要用這個鹽。
他講在他小時候,時常把這種晶體鹽含在嘴里當零食吃,一邊說還一邊提醒我也嘗嘗。我挑了一顆很小的顆粒含在嘴里,鹽塊兒化得很慢,沒有那么強的刺激,當零食吃還真能接受。老人朝鍋里放了一小塊鹽,然后非常熱心的把剩下的鹽都要我打包帶走。還說:“你喝黑茶,一定要用這個才好。”盛情難卻,我沒有拒絕。
電鍋熬茶是自動化的,熬沸了之后就是恒溫加熱。在這個間隙里,他又開始在儲物間里尋找一些老茶具。一個包得嚴嚴實實的包裹,經老人小心翼翼的拆開,里面有一把老壺,幾個老碗。其中有一個老碗,是他父親留下來的。在他的記憶里,他的父親就是穿著行商的袍子,有個碗套專門裝著這個碗,別在腰間。早路邊歇腳的時候,掏出碗喝口茶,餓了放塊酥油,加點炒面。那個碗雖小,卻裝著他們這個家族先輩們走南闖北的記憶。

也許老人是想給我最有深度的體驗,所以一再強調,喝熬茶一定要用老碗。茶熬好了,他用一個勺子舀到碗里,自己先嘗了一下,然后提醒我說可能有點咸。他給我用的是一個醴陵瓷的老杯子,前不久我在新聞上看到,安化縣的領導和茶葉協會去醴陵做了考察,好像茶和瓷達成了一些合作。這些事產業外的人并不關心,但是我手中拿著的這個醴陵瓷杯,底部寫著1969的字跡。醴陵瓷和安化茶,很多年前就一起在千里之外回族人的生活方式里邂逅了。
我嘗了一下,沒放奶的熬茶,但因為各種滋味的料放了很多,混在一起,大口喝上幾杯,依然會渾身發汗。回族人禁酒,行走在高寒戶外,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驅寒。講起自己為什么會定居在西寧,也是一段令人感慨的往事了。他的父親一直在陜甘青之間經營著茶葉,談到祖籍,他說他應該是陜西人。但是因為父親一直在青海做生意,最后舉家就留在了青海。
老人在政協文史館,和青海當地關注茶文化的很多人都有交集,談及回族傳統熬茶,他也很多次憑借著自己的記憶熬給很多人喝過。辛、辣、醇、甘,一碗熬茶里,煮沸的是當年那些坐賈行商才能深切感受到的滋味。雖然,茶如人生的這個話題很老套,但是走了這么多地方,不同的人對同一個茶都會有更適合自己,更恰如其分的發揮與表達。這無關年齡,無關民族,無關地域,回到自己最真實的生活場景,你就會相信歷史的選擇。
上一頁
下一頁
上一頁
下一頁